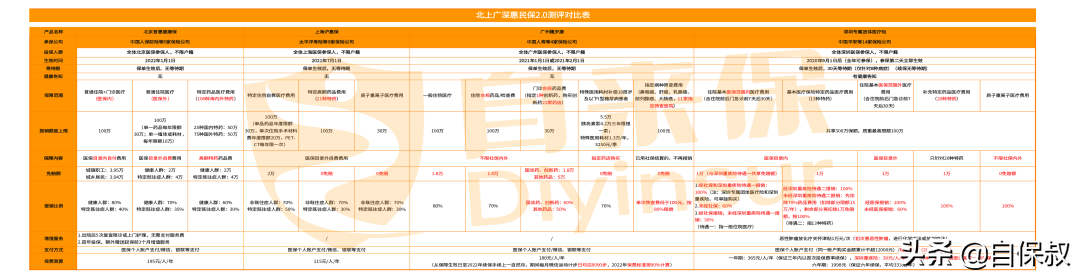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牙膏推荐
孙江读王笛《中国记事》——叙事的力量
皓齿牙科网
2026-01-09【牙膏推荐】158人已围观
简介在呼唤叙事的复归时,微观史大家金茨堡()曾尖锐地批评过往的历史学道:“自伽利略开始,自然科学的定量和反人类中心的方法使人文科学处于令人不快的两难境地:要么使用弱的科学标准,能够获得重要的结果;要么使用强的科学标准,获得不重要的结果。”确实,在科学导向下历史主体处于休眠状态。作为中国微观史研究的重要学...
在呼唤叙事的复归时,微观史大家金茨堡()曾尖锐地批评过往的历史学道:“自伽利略开始,自然科学的定量和反人类中心的方法使人文科学处于令人不快的两难境地:要么使用弱的科学标准,能够获得重要的结果;要么使用强的科学标准,获得不重要的结果。”确实,在科学导向下历史主体处于休眠状态。作为中国微观史研究的重要学者,王笛的《中国记事》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他者”(other)的视线。幽闭在洞窟中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倒影,他者的视角不仅能弱化本质主义叙事带来的沉闷,还可以提供重新认识自他关系的契机。王笛擅长绘画,曾在自著里展示过所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海登·怀特、费正清等十九位历史学家的素描,惟妙惟肖。王笛绘画的本领也反映在本书的叙事上,《中国记事》八部二十九章,仿佛手绘的一张张卡通片,连缀起一部别样的分叉的历史。
撰文|孙江(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讲席教授)
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把学人分为两个类型:刺猬和狐狸。前者一以贯之,是一元论;后者灵动善变,属意多元。伯林以结果论学人,竟发现自己无法归入任何一类。在我看来,如果按照学者的作业方式,似可分为如下两个类型:农耕型和游牧型。农耕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品如醇酒,历久弥香;游牧型逐水草而生,苟日新日日新,我变故我在。在我熟悉的学者里,王笛无疑属于农耕型,晨起即书,两小时后方才洗漱早餐。正是如此勤勉不懈,王笛每有新作问世,或聚焦四川,或深描成都,写到快与研究对象同一化成了“四川王”或“成都王”。王笛是那种待在房间里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的学者。四川人嘛,只要有麻辣,吃啥都一样。
不过,翻阅案头散发着油墨香的《中国记事》(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看法稍有动摇。这本“跨出封闭的世界”——不以四川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凡八部二十九章,从1911年辛亥革命写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8年,也就是说,涉及绵延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的坍塌到现代党国体制的确立这一时段。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被称为军阀混战;军阀割据不假,混战实为夸大之词,因为军阀之间很少真枪实弹相向的。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思想、文化、经济乃至政治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我一向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确切地说是北京政府时期——堪称中国现代文化的“轴心时代”,形塑了现代中国的轮廓,换言之,现代中国的基本命题都可从这一时段中找到。惟其如此,这段历史犹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所说的“分叉的历史”(bifurcatehistory)的临界点,值得学者深描细述。
“比胜利更伟大的是中国的觉醒”
《中国记事(1912-1928)》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4月
第三部五章写1919年巴黎和会前后的博弈。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当收回被德国攫取的权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这让中国抱以很高的期待,但最后重重的落空。王笛引用塔奇曼的话指出,巴黎和会让中国看清了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外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看似偶然,实则有帝国主义国家间利害交换之必然。在巴黎和会上,寡言的日本代表提出了三个议案——关于山东权益、关于南洋诸岛以及废除种族歧视法案,后两条特别是最后一条,据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广部泉的研究,恰是列强与日本妥协的一个原因所在。第三部最精彩的莫过于一个小人物“王先生”(伯衡),他向《》投书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引来了一番论战。以公共史学为写作旨归的王笛,在此发挥了职业史家考索探幽的本领。
第四部三章讲中国的觉醒。巴黎和会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会议期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王笛称之为“巨人醒来”。确实如此,五四运动从命名到赋予其意义都体现了自我规定的主体性。在一般性的叙述之外,王笛发挥了微观史家的本领,挖掘出纽约《文摘》上报道的名为马骏的南开中学学生领袖的故事。马骏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倾向共产主义,后赴莫斯科接受培训,回国后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8年死难。这个鲜为人知的人物,诠释了五四后中国政治风向的转变以及一代为共产主义理想捐躯的知识青年的形象。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文化和思想上的冲击,美国专栏作家充满期待地称,“比胜利更伟大的是中国的觉醒”。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观察历史的多元视角
巴黎和会上中国落空的希望在下卷第五部有了新的展开。1922年2月,由美英主导的华盛顿会议签署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日本交还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自主地从汉口和山东半岛撤军。华盛顿会议没有巴黎和会上的紧张感,在素描了相关情景后,王笛回到“个”的视点,写美国报章上的报道,写在美华人和留学生的动向。第一章登场的司徒雷登和史迪威再次出现。此时的司徒雷登正在北京忙于筹建燕京大学,请来了著名设计家亨利·墨菲,后者设计了雅礼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20年9月,史迪威携家带口来到中国,作为语言教官的史迪威曾在山西修过路,目睹过日本人的跋扈。赛珍珠从华北到了江南,细心观察民间烟火,留下了一桩情杀记录。1921年赛珍珠的母亲在其老家——“镇江”去世,被埋葬于她经常经过的外国人墓地。晚年赛珍珠回忆起墓地三位不知姓名的水手墓碑上的碑文:AsIamnow,somustthoube;Thereforepreparetofollowme(而今我先下黄泉,他日来此轮到你),这段话显然出自拉丁谚语——Tufui,egoeris(我曾经是你,你将会是我)。
王笛很善于讲故事,在打打杀杀中适时插入弱势群体——女性的片段,一方是被卖的丫鬟,一方是女性参政的诉求,在这种充满张力的魔幻世界里,王笛以赛珍珠的笔端转述了一个年轻男佣和两个寡妇佣人的故事。赛珍珠的佣人李嫂软禁了男佣,在赛珍珠的撮合下二人虽然“结婚”,但男佣心念另一女佣;由于担心“丈夫”逃走,李嫂在一次争吵后又将其囚禁。赛珍珠责怪李嫂不该囚禁人,李嫂说:“他还想要另外一个女人——要我们俩”。赛珍珠答曰:“很多中国男人不都只有一个妻子!”李嫂坚定地回答:“不行”。闻后赛珍珠很是感慨,革命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一般民众中。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为何写史?如何写史?
不消说,写史的目的首先在追求“真实”。事实有两个层次:实在的和表象的。实在的事实是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本书的他者——美国人耳闻目睹的事实是表象的事实,受到当事人的视点、职业、意识形态等制约。王笛在前言引用费正清的话作为题头语颇具深意:“长期以来,美国试图让中国变得更像自己。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尝试尽管屡屡失败,却仍然锲而不舍地努力”。这是战后美国人在总结美国为什么失去中国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在充满变数的历史过程中,历史的结论未必是历史演进的主格调,也未必是执拗的低音。他者表象的事实可一分为二,一为被证明是客观的正确的,一为被证明是主观的有误的,二者中我更属意后者,不仅因为正是后者的不断叠加导致了费正清所说的结果,更因为后者包含了当事人自以为是的主观判断。如凯蒂女士对中国妇女在新时代已有的和将有的作用所做的满怀激情的演讲——“因为她们的积极参与,清政府才被推翻,共和才能建立。现在她们要求选举权,否则她们将使用武力”。这种带有对未来期待的事实含有当事人对所见之事的价值追求,蕴藉了观察者的主观期待,涉及到追求真实的目的为何之问题。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如果仅止于真实和真理,历史书写这一行为就可以完全归入科学了,正如马克·布洛赫对何为历史给出的另一个回答——美感——所表征的,历史书写是有伦理指向的,真正打动人心的著作不只在文字修辞上,更需要写者与被写者之间心灵的碰撞——真情。王笛的叙事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均有精巧的安排,绝不放过细节和微声。前述赛珍珠回到南京后,看着南京国民政府忙于粉饰大街小巷,感叹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是多么为他们深爱着的国民感到羞愧,而这种羞愧又是多么动人而可怜啊!”这句看似平淡的摘译,读后令人浑身震颤。
读罢本书,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另一个问题是,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换言之,如何在当下的历史书写中给本书定位?《中国记事》是一本独特的断代史。所谓“独特”是指本书是以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历史,与通常以中国人的叙述为主要资料的历史著述很不相同。从本书的铺陈看,他者眼中的中国历史未必不客观,与中国人讲述的历史未必截然二分,这说明当时的美国人的中国认识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有交错的,更根本的是,历史叙述具有基于人的同一性而来的普遍性特征。缘此,我强烈推荐习惯于同质化历史的读者阅读本书。即使从获取知识的角度而言,打开本书也能得到难得的新知,如1915年的《二十一条》是何时消失的?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
与一般的通史著作不同,《中国记事》言必有出处;与一般的专著别异,为了阅读方便,《中国记事》没有繁琐的征引,阅读之下,颇有非虚构写作的感觉。伴随历史作为“消费品”需求的增大,时下非虚构写作颇为盛行。我在多处讲过,非虚构写作绝不是历史和小说之和,也绝非把事件写成动人的故事。非虚构写作是基于有限的证据和合理的推论而来的知的冒险,在历史的空白处宣示主权。在此意义上,《中国记事》颇有正本清源的示范作用。
校对/杨许丽
很赞哦!(97)
下一篇:美少女的舌侧记录